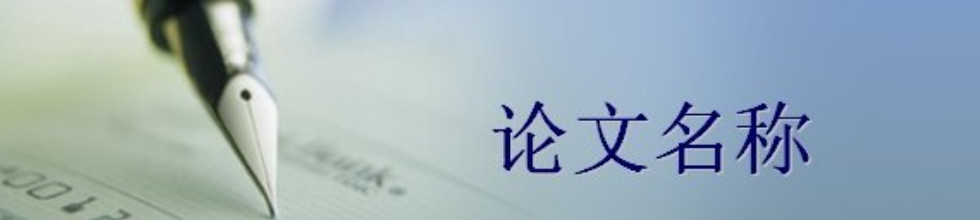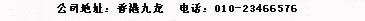话说李新顺
原文刊登于《剧本》年第7期
李新顺,剧团厨师。大家都喊他李师傅。
李师傅,安阳水冶人。水冶和林县(今林州市)相挨很近,但两地口音却不大相同。李师傅在林县工作多年,口音基本没改多少。我刚进剧团那会儿,猛一听他那水冶腔,既觉得奇怪,也感觉好笑。想不到,天底下竟还有这样说话的人。现在想想,我那时候就一山里小孩儿,没出过门,没见过世面。衡量一切事情,爱拿自己熟悉、了解的做标准。遇到不符合的,感觉奇怪,感觉不可思议,也属正常。就像阿Q,见城里人把“长凳”叫做“条凳”,他认为是错;看到城里人油煎大头鱼,加上切细的葱丝,他觉得可笑。一样道理。
去年在新疆,听来一个故事。有学校组织偏远地区的孩子进了趟北京。回来之后,老师要求孩子们写作文,谈谈对北京的印象。很多孩子在作文中感慨,北京好是真好,就是太偏僻啦!——这些孩子,和我当年一样,是以自己为中心的。
李新顺是个大高个儿,特别是他那两条腿,长得很长,按现在的时髦说法,是标准的大长腿。单凭这身材,李新顺是具备了享用“高大英俊”这一赞美词汇的条件了的。很可惜,他不能。一切都被他那两脚上的“鸡眼”给耽误了。
脚上长“鸡眼”,这事儿很普遍,但能够像李新顺那样,达到“层出不穷”,还真不多。起先,他左脚先长了一个。好办,剜喽!没想到,伤口尚未愈合,右脚也长了,而且,一长就是俩。没办法,再剜喽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他那两只脚,像是在搞“长鸡眼”比赛,左右交替,此消彼长,一发而不可收。最终导致,他那两个脚底板儿上,“刀疤”和“鸡眼”并存,几乎已经千疮百孔。剧团老书记对此形容说,新顺这两只脚,已经是星火燎原啦!
脚底的“刀疤”和“鸡眼”,严重影响了李新顺的正常行走。前脚板不敢着地,着地会疼。于是,他就只好翘着脚尖,用脚后跟着地,一步一步,往前挪。久而久之,两条大长腿,为了平衡身体,变弯了,直溜的上身,也佝偻了。就这样,一个“高大伟岸”的身躯,逐渐变成了“猥琐不堪”。好在李新顺就是个厨师。不需要练功、翻跟头,不需要出头露面,登台见观众,腿脚是否灵便,模样是否标致,都不影响他围着锅台做饭。
除了脚底的“刀疤”,李师傅脸上还有一道“疤”。位置在右脸颧骨处,呈三角形,暗黑色,很深。更神奇的是,他这道“疤”会随着李新顺的情绪抖动。他生气了,那“疤”抖;他开心了,那“疤”抖;他安静了,那“疤”也抖,而且抖动的频率会加快。关于这道“伤疤”的来历,说法有两种:第一种,淮海战役期间,李新顺被中央军抓了壮丁。在前线挖战壕,他耍滑偷懒,被班长发现。班长一怒之下,抡起一把铁锨,手起锨落,李新顺右脸上就留下了这道永久的纪念;第二种,更邪乎。说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之前,在大陆埋伏了一批特务。李新顺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脸上的那道“刀疤”里,埋藏着国民党的微型电台,他每次抖动,就是在向台湾发报。有几个老师,甚至怂恿我们小孩子说,贴着李新顺的右脸仔细听,就能听到“嘀嘀”的发报声。
这两种说法,没有人当真。特别是第二种,更是没人信。所以,多少年以来,无论领导,还是群众,没人找李新顺落实过,李新顺也从来没向任何人解释过。大家当笑话说,也当笑话听。大家呵呵大笑一阵,李新顺的脸上那“疤”抖几下。风一吹,过去了。但是,谁也没想到,“文革”中期,李新顺的一个举动,却把林县剧团的上上下下、老老少少给惊着了。
事情的起因,是一位年轻的革委会副主任,和李新顺开了个玩笑。这位副主任,为人严肃,平时总是绷着脸,从不与人说笑、打闹。他那一天,也不知搭错了哪根筋,竟然和李新顺开起了玩笑。他走进厨房,对正在做午饭的李新顺说,县公安局刚才来电话了,说他们已经掌握了你向台湾发送电报的证据,要求你现在,背着行李,去监狱报到。
在场的几个人听了,捂嘴想笑。李新顺听了,片刻沉默。在“刀疤”快速抖动一阵之后,他解围裙、洗手,回宿舍,扛起铺盖,蹒跚着向公安局去了!——在场的其他人,傻了;那位革委会副主任,慌了。一时手脚无措,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临到底,还是多亏剧团老书记出面,派人撵上李新顺说,经过剧团领导班子的讲情,公安局终于同意,你可以先在单位进行劳动改造,暂时不用去住监了。老书记还特意叮咛派去的那人,表情要严肃,态度要认真,千万不能让李新顺看出来,这是开玩笑,否则,会显得剧团领导班子不严肃。
就在县公安局的大门外面,李新顺又被“哄”了回来。回来之后,他还是一句话没有。一步一步,挪到小屋,放下行李,回到厨房,勒上围裙,洗洗手,做饭去了。然而,大家伙儿,却被李新顺主动投案的行为,彻底给闹迷惑了。就此事议论了很久,猜测了很久,有人开始怀疑,他那道“疤”里兴许果真埋有电台。甚至还有人建议党组织,应该找李新顺谈话,劝他主动交代,落一个坦白从宽。老书记听了,扑哧一笑说,放心吧,国民党瞎着眼,也不会找李新顺这样的人做特务。
这件事情,虽然就这样不了了之啦,但仍然有人纳闷、不解,既然没有埋藏电台,为什么别人吓唬一句,李新顺就会主动投案?还有,他脸上的那个“疤”,到底怎么来的?至今是谜。至今无解。
李新顺三十多岁了,还是单身。那时候,剧团演职员,是真把剧团当家的;剧团的领导、老师,也是把自己的员工当亲人待的。剧团有人单身,剧团领导和家里的父母一样着急,更何况,李新顺早就没了爹娘,所以,剧团领导就更加地用心用力,四处为他张罗媳妇。也是李新顺命好,恰好有一个离婚茬儿,方方面面都很般配。剧团班子几个成员,跑前跑后,帮他撮合。几趟下来,亲事说成。眼看要举办婚礼了,李新顺却还没凑够钱。情急之下,剧团召开大会,领导动员大家捐款。每人拿出五毛钱,帮助李新顺成了家。
在农村,给儿子娶媳妇,是爹娘的职责。应该爹娘做的事情,在李新顺这儿,剧团的伙计们承担了。有爱开玩笑的人就说,那咱们大家伙不就成李新顺的爹娘了?这类玩笑,在剧团不愁没人起哄架秧子。于是,就有嗓门大的人高喊:李新顺他爹——!旁边听到的,不失时机,一个个伸长脖子,齐声答应:哎——!再往后的日子,这似乎成为了一道固定节目。每当饭时,大家拿着碗,敲着筷子,来到食堂门口,这边呼爹,那边答应。哈哈一笑,盛碗吃饭。有一天,有个唱丑的演员突然改口,喊道:李新顺他娘——!一个性格豪爽的女演员,也没听清喊啥,张口就答应:哎——!惹得大家一场哄笑。有人打趣说,她这一声答应不要紧,硬是让李新顺成为了爹多娘少的人。
李师傅对此,表现得很平静。不恼怒,不记恨。大家伙再怎么闹,他那里永远是默默地做饭、打饭,默默地刷锅、洗碗。时隔多年之后,我分析李新顺,他肯定明白,大家的玩笑没有恶意。还有,那些爱和他开玩笑的人,论年纪,也是他的长辈。喊这个一声爹,喊那个一声娘,不吃亏。更何况,剧团老少爷儿们的那份情义,是实实在在的。五毛钱,在六十年代初期,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
李新顺的媳妇叫珍。姓什么,我忘记了。她的大概模样、轮廓倒还记得:中等个头,长方形的脸儿,穿戴得干净、利亮。珍爱说爱笑,说话声音很大,笑起来声音也大。珍和新顺日子过得很恩爱。他们有三个女儿,模样、脾性都随她们的娘。珍每次到县城来看新顺,三个女儿都会跟着。剧团院子里有苹果树,如果苹果熟的时候,新顺的三个女儿恰好来了,剧团老书记会指派人捡红透了的苹果,摘一小筐,再用井水洗洗,送到李新顺的小屋,给三个孩子和珍吃。三个孩子在院子里玩儿,谁家有了稀罕零食儿,也会赶紧拿出一点,塞到新顺女儿的手里。那时候的人不富裕,剧团里的人,也并非个个都大方,但对新顺的女儿们,他们谁也不吝啬。还有平日里,那些爱和李新顺开玩笑的人,这几天也会变得很规矩,一句玩笑没有,不会再敲着碗筷乱喊,也不会再拿着新顺脸上的“疤”说笑话。
大家懂得,在他媳妇和女儿面前,要给新顺留面子。
责任编辑:武丹丹
图片来自网络
杨林赞赏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mauritiustour.net/jbszzmz/2213.html
- 没有推荐文章
- 没有热点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