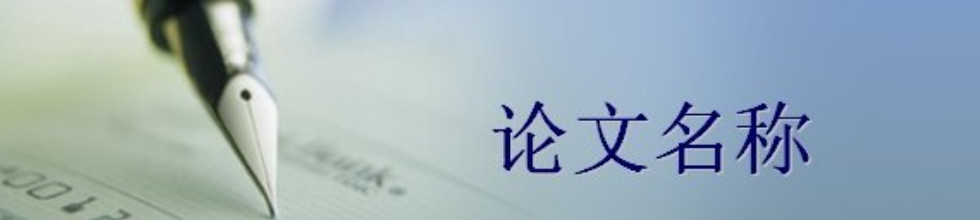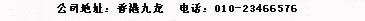彩虹散文父亲的腿脚
院子里满树的麻雀叽叽喳喳地一叫,我家的天就算是彻底亮了。每天最先起床、最先开门的,永远都是父亲和母亲。即便是雨、雪天,他们也很少睡过六点半。起床后,一个人打扫院落,另一个人烧火做饭,就是年过七十后,他们依然保留着“黎明即起”、“日出而作”的良好习惯。
黎明时分,窗外一串细碎的脚步声将我唤醒。天还没大亮呢,父亲急着起来干啥?不就是开个大门、扫个地嘛,如今,家里既没孩子急着上学,也没人赶着下地,晚一点起床又有什么关系!
“咪咪—咪咪--”,听到母亲唤猫的声音,我才意识到,刚才那还算轻快的脚步声,根本不是父亲的。这会儿,左胯骨粉碎性骨折的父亲,已经在门房的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了。哥哥说,父亲以后可能再也下不了床、走不成路了!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今后要想再听到父亲的脚步声,恐怕已经很难了!
年轻时,父亲是个腿脚轻快的人。性格开朗、热情好客的他,一天到晚,腿脚都很难闲着。母亲不满地抱怨说:“他一天到晚腿脚不闲的,可又干了多少正经事嘛?!他整天走东家、串西家地被这家拉着帮厨,被那家求着说媒,耽误了咱多少功夫!”由于父亲的缺席,家里的琐事,地里的庄稼,许多本应由两个人共同去挑的重担,好多都转移到了母亲的肩上。
厨艺好、会撮合,是父亲最显著的两大优点。逢年过节或者婚丧嫁娶,自家的亲戚朋友、周围的邻里乡亲,谁家要来亲戚,谁家想过大事,只要割了肉、支起红案,父亲就要花上几天功夫不分早晚地煮肉、装碗,准备席面。亲戚们吃好了,主家的事也就算过好了。人家的事忙完之后,给一个洗脸毛巾、送一盘白馍,就算是对他几天辛劳的回报了。
父亲的另一大功德,就是为本村人成全了许多姻缘。懂世理、观念新、能说会道、善于平衡各种关系,是父亲不同于周围人的明显优点。这些优点,成就了他善于说媒的名气。
说媒牵线,那是中国几千年来促成婚姻的最主要的方式。对于过去足不出户、在家待嫁的姑娘们来说,靠丢玉簪、翻墙私定终身的,毕竟只是戏曲舞台上的崔莺莺、张生们。就是同窗了多年又相知相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,也难以左右自己的婚姻。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,那是一张全社会编织了几千年的罗网,那是一道多少代人都难以突破的防火墙!
千里姻缘一线牵,能成人之美的月老、红娘,本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。可解放后《婚姻法》的宣传,却将这一成人之美的角色描成了花脸。懂事后,我不愿意父亲再给人说媒。母亲说,那能由得了他?许多人家都是双方基本上看好了之后,硬要请他出面、吃席的。就是婚姻能自主了,许多父母仍觉得请媒人、遵礼法比悄悄默默地私定终身更有颜面。
有一家有六、七个姑娘,三、四个都是他当的媒人。我好奇地询问原因,父亲说,那家当家的男主人只信任他。挨帮的姑娘们一个个长大了,不管是谁提的亲,姑娘们的父亲都要郑重其事地上门央求他去当媒人。人家说了,只要他出面,一切都好说;只要他搭话,彩礼也好商量。
还有一个姑娘,第一次姻缘是他牵的线,中间出现了不光彩的变故之后,男方的父母黑着脸上门来质问。靠面子吃饭的父亲非常恼火,他陪着笑脸道着歉,好话说了一蒲篮,最后总算是退了彩礼、退了婚,息事宁人。那一桩没成的婚事,让父亲生了一肚子气。他当时就发誓,以后再也不给人当媒人了!可随后不久,父亲那比父母还亲的干爹干娘又为了那个姑娘上门求他。被伤了脸面的他,坚决不答应。他们关着大门在院子里嘀咕了半天,干爹干娘恩威并施,一会儿恳求,一会儿规劝。最后,被缠得脱不了身,他只好又骑上自行车,来来回回奔波了几个月,直到将那姑娘嫁到了邻村。
说媒,最费的不只是来来回回不断折腾的腿脚,而是讨价还价的口舌、黑一阵红一阵的脸面。跑路,对于腿脚勤快的父亲不算什么。一趟一趟地在男方和女方家穿梭,虽然双方都在有酒有肉地支应着,但只要谈到彩礼,就得一点一滴地争究着。既然是谈判,就难免伤脸。而一旦说高了,就要立即回过头找台阶下。谈婚论嫁时,利益固然重要,但也要顾及彼此的家境和脸面。介绍完男女的长相和才能,再论双方的父母和家庭。能互相欣赏最好,小的欠缺还得各自让步、互相包容。在谈判中能不伤和气,在体谅中能彼此满意,父亲的这种能力,使他说媒的成功率颇高。善于说媒的父亲,忙活上一阵后,给我们挣回来的,大都只是一碟子媒人馄饨、一方擦嘴的手帕。人人都说媒人费鞋,要不停地跑路,但很少有人给他买过鞋。父亲的付出,最主要的回报是人缘好。
改革开放后,村里又开始搭台子唱戏、过赛缚秋千。这些让全村人热闹的公益活动,大都没有经费。每次过事,都得村里德高望重的人一家一家地去筹款,一户一户地去借东西。父亲不会唱戏,也不善于缚秋千,但化缘、借东西一类的差事他总爱承担。因为人缘好,只要他出面,一般都很少空手而回。所以,我们经常取笑父亲,自己虽然不会唱戏,但总是从人前忙到人后。戏台子都拆了,他还忙不完。凡是他借的东西,事后他也要眼看着再给人家还回去。
母亲对此有些不屑,她觉得,就是全村人把你说得再好,咱自家的日子还是要靠咱下苦才能过好!
父亲走路腿脚轻,他从窗台下经过时我们很少能听到刚健有力的脚步声。母亲小声地数落到:“轻腿轻脚的,没一点阳刚之气!走起路来脚不往起抬,噗嗒噗嗒地哪里像个男子汉?”一说到这个话题,她也就要趁机教育我们,走路时一定要把脚抬起,别拖着鞋刺刺拉拉的没一点朝气!
父亲的腿脚虽然不是掷地有声的力量型的,但这在更多人的眼里也不是什么大的缺点。腿脚轻快的他,爱跑,爱串门,爱与人交往,喜欢和人攀谈。不管走到哪里,迎接他的都是亲切的招呼、一路的问候。跟着他走亲戚,不论远亲近亲,每家都很热情,都很诚恳。闲聊时,他总爱细数每家人对他的好。我对他说:“世上哪里会有无缘无故的好嘛!人家对你好,那也是你拿你的好心和殷勤换来的。你把谁家的事没当事嘛?给谁家行门户,你都是要走到人前头去的。关照我干婆干爷,周围的亲友谁有你跑得勤、送的吃喝多?我老姑去世后,咱行的门户,引得他们一村人羡慕夸赞!就是我老舅家,你那些血缘关系有些远的表哥表弟,也被你走得比亲的还热乎、还周全。”
对周围的老人都很好,这又是父亲一个让人称道的优点。对祖母的日常照顾自不必说,就是对住在几里路之外的老姨、老姑,腿脚勤快的他,也要隔三差五地骑着自行车去看望。到街上买点吃喝,坐下来嘘寒问暖,遇到小事搭把手,有大事时帮几天忙,他的出现,是一个个老人最暖心的期盼。
提起外公外婆,父亲一辈子总是满怀敬重、赞不绝口:“你看人家的为人,你看人家那家教!”外公家的日子虽然清贫,但老老少少从没怠慢过他;我家的祖母虽然爱生是非,但他的岳父岳母从没找过麻烦,也没让他难堪!他虽然有时会对老婆吹胡子瞪眼,但他背着老婆经常在我面前夸赞母亲的贤惠与能干。母亲对我家的贡献,他也都悄悄地回报给了外公外婆。
父亲年轻时我们家穷,除了殷勤和笑脸,他给老人也拿不出更好的孝敬;而一旦外家要过婚嫁一类的大事,善于烹饪的父亲,总是要系着围腰在后厨间通宵达旦地忙活好几天。待我家的日子宽松之后,外公已经去世了,只剩下年迈的外婆。不管是做了让人稀罕的饭菜,还是摘了时鲜美味的瓜果,他都要跑着给老人送去。父亲的殷勤,不但让老人感到温暖,老人身边的小重孙们也经常跟着沾光。几天不去,那些嘴馋的娃娃就会守在门口等待,去和老人念叨。能跟着姥姥蹭几口吃的,他们对姥姥的女婿也充满了期待和爱慕。
但在母亲的眼里,腿脚快,却是父亲的一个缺点。腿脚快的他,常常是一转身就不见人了。尤其是下地干活,他总是对母亲说,你先走,我后头就来了。干上半晌活,还不见他的人影,母亲就有些恼火。母亲下地去了,父亲也锁门出巷。走在田间的小路上,他东家看看,西家瞅瞅,碰到话多的,还要停下来聊一聊年景收成,说一说日子的丰歉。谁家的庄稼做得好,谁家的地里长满了草,谁家的苹果经管得周到,谁家的地水没浇到,一进地,他都会向母亲一一报道。母亲不满地抱怨道:“那跟咱有啥关系哩!你就会躲奸溜滑,把我当大头捉!”
和母亲聊天时,我们经常感叹,父亲是个会享福的人,他应该更适合城市生活。他不是个体力型的壮汉,但他绝对是个会生活的细人!就是一辈子蜗居在农村,他的精神生活也比周围的人丰富。
他不喝酒、不打牌,也不太抽烟。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爱跑、爱转、爱看热闹。哪个村子演戏,哪个乡镇有交流会,他都会骑上自行车约几个人去转去看。我小时候的许多乐趣、见识和口福,都与此有关。
记得有一年初冬,县上举办多年罕见的物资交流会,骑自行车赶50多里路是很费力气的,一般人嫌远都不敢去凑那个热闹。父亲的兴致很高,他用自行车驮着十来岁的我一起去上交流会。那一次远征,是我第一次去遥远的县城。
初冬的庄稼地一片荒凉,冷风嗖嗖地直往衣服里钻。我缩着脖子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,几个小时的颠簸,坐得我腿脚发麻,屁股冰凉。坐累了,跳下车走一段路,我腿脚麻木得只剩下了落地时隐约的痛感。那时的我,还没见过山。那一处山地蓝幽幽的,很好看。有一段山石嶙峋的路,很窄很险很难走,但我觉得很新鲜。我们擦着凸起的岩壁小心翼翼地通过,那条灰白色的石头路好像是刚凿出来的,岩壁上突兀不平的棱角锋利而冰冷,一不小心,就能把人划伤。那段路,走得我刻骨铭心。早饭后出门,到县城时已临近黄昏。我们在人山人海的露天剧场挤挤撞撞地看了一会儿戏,后边的人都站在凳子上,我们就是踮着脚尖,透过黑压压的人缝,也没看出多少名堂。初冬的夕阳怯生生地泛着乏力的昏黄,父亲提醒说,天快黑了,我们还得去找个晚上落脚的地方。
跟着父亲上交流会、看戏,主要是图个热闹、看个新鲜。戏台上那些身着古装扭扭捏捏的人物,那些拿腔拿调老掉牙的故事,对奔着稀罕来看的娃娃们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。所以,到哪里看戏,路上的景致往往比戏台上的角色更为重要,戏园子边上的小吃摊比舞台上的剧情更有吸引力。
多年后循着记忆回想,父亲带我走过的那一片幽兰的山地,那一条让我印象深刻的石头路,到底在哪里呢?以后几十年在全县穿梭,咋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一方景致呢?难道那是一个熟悉的梦境?有一次跟哥哥提起,他说离县城不太远,的确有那么一个地方,那里出产的石头很有名。
大学毕业后,我落脚到了渭南。几年之后,结婚生子的我,也为父亲的生活拓展出了一个全新的空间。为了给我看孩子,他经常要在家乡和渭南两地之间辗转。
孩子断奶后将他送回家,父母亲满腔热情地接纳了那个才一岁多一点的娃娃。孩子一岁之前,都是我请假在家一个人带他。第一次丢下他转身离开,孩子声嘶力竭地哭叫着在母亲的怀里挣扎,父亲将孩子抱进自行车前的座架上,带着他满村去转。孩子的哭声听不见了,我才忍住眼泪走出了村庄。
替我们管孩子的那几年,对于父母亲来说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。接管外孙时,家里的孙子还不满一岁。男孩子好动,两个不懂事的小兄弟相遇,吃饭要一起趴在炕墙吃,睡觉都要挨着祖母睡,在被窝里要笑着闹着互相磴,在炕上要喊着嚷着一起耍。两个男孩吃着吃着便会争抢,耍着耍着就免不了冲撞。一天到晚,父母手忙脚乱难得清闲。夏天的中午,又热又困,忙活了半天后,就是想睡个午觉,也经常很难如愿。面对父母的辛劳,我于心不忍。母亲安慰我说:“没事,乱马都要从桥上过哩!一起带也有一起带的好处,过上几年,齐刷刷的也就都长大了!”“可是眼下这每一天,忙忙乱乱的,腰酸背疼的,你们可怎么过呀?”父亲说:“熬时间嘛,熬上十几个小时,一天就过去了!熬上三年,娃娃就都该上学了!”
那几年,母亲的心思全都用在了两个娃身上。一直在乎庄稼的她,将地里的活几乎全丢给了父亲。母亲经常说:“娃比啥都重要!从小把娃管好了,娃以后的身体就没问题。人家现在的娃少,必须先把娃管好,地里的庄稼能收多少是多少。”
那几年,母亲在全力以赴地照顾两个孙子,辅助母亲的父亲也没有少忙活。地里的庄稼只剩下他一个人经管,家里的锅碗瓢盆他也没有少摸。母亲看孩子,他做饭;母亲给孩子洗衣服,他扫院;一个孩子哭闹,他就抱着另一个出去转……
孩子在家放上一个多月,父母亲就会把孙子带到我们身边再倒换一段时间。到城里来带孙子的大都是孩子的奶奶,而作为爷爷的父亲并不拘泥于那些陈旧的观念。有一天,楼上看孙子的几个老人聚在一起聊天,抱着孩子的父亲说:“人家啥时候再还需要咱嘛?咱还能再给人家帮个啥忙嘛?不就是管个娃嘛!再过几年,你就是想给人家帮忙都帮不上了。”
一到节假日,不用看孙子了,父亲喜欢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不紧不慢地全城去转。古旧的老城、闲适的公园、热闹的广场、街边的小摊,他都喜欢一个人随便去转。到小桥那边的旧货摊上,去搜寻一些不常见的玩意;在广场旁边,吃了个零嘴尝了个稀罕;在公园里听一拨人唱戏,在街边看了一些新鲜……腿脚麻利的他,将一个个节假日调节得有滋有味、丰富多彩,一如他善于烹调的饭菜。
那时候,父亲最爱吃的是渭南的水盆羊肉。早上起来,背着孙子高高兴兴地去吃羊肉泡。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汤羊肉端上桌,将刚出炉的烧饼掰碎了泡进汤里,爷爷刚捞起一块肉,眼尖的孙子立即兴奋地喊道:“肉肉!肉肉!”第一块肉给孙子喂进嘴里,孙子在有滋有味地嚼着,爷爷吃了一块泡馍。爷爷刚夹起第二块肉,还没腾利嘴的孙子又开始喊叫:“肉肉!肉肉!”在孙子激动的叫喊声里,爷爷笑着嘟囔了一句:“这怂娃!”但还是将肉又喂到了孙子的嘴里。一碗水盆羊肉,总共才能有几块肉嘛!孩子嘴馋,爷爷也心疼孙子,最终,肉大都让孙子吃了,爷爷只剩下喝汤、吃馍了。那几年,爷孙两个搭帮去吃水盆羊肉,爷爷大都只落了个虚名。
爷爷爱孙子,从来不在嘴上体现。父亲是个爱干净的人,他打扫的院落,他收拾的房间,他穿的衣服,从来都是干净利落、四棱见线。见不得邋遢的他,却从不嫌弃孙子们的残羹剩饭。每顿饭吃到最后,几个孙子都难免会剩饭。孩子们碗里的剩饭,常常被戳得乱七八糟的,如果没有他稀罕,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随手倒掉。端起孩子的剩饭,父亲经常说:“我娃娃的剩饭,我不嫌脏!”看他津津有味地吃着孙子们的残羹剩汤,我常常感慨,人要是心里爱了,就啥都不嫌!如果感情不到位,就都是弹嫌!
和孩子们亲近,父亲还有一个习惯,那就是喜欢捧起孩子的光脚丫去闻、去亲。“来,让爷爷闻一闻你的脚丫子,看臭不臭?”他将自己的脸捂到孩子们的脚丫上,然后深深地吸着气,一脸沉醉地闻着、亲着、笑着,最后再用下巴上微青的胡茬去蹭孩子的脚心。孩子痒痒得咯咯大笑,他也很夸张地说到:“我娃这小脚臭得很呀!呸呸呸,臭得很!”看着幸福的爷孙俩,全家人也满脸是笑。
两年之后,满三岁的孩子要上幼儿园了,父母才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母亲说,管孩子最累的不是身体,而是心!管父母不在身边的孙子,除了孩子的冷暖吃喝,还得担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。昼夜睡不了个安稳觉,那都不算啥,万一出点差错,给人家的父母不好交代!
孩子上学之后,父母的生活恢复了正常。春种秋收,他们平时很忙。放暑假的时候,孩子会回家和他们住一段时间。冬闲了,反复邀请,他们才会来渭南住上几天。那时的父亲最为轻松。把渭南转遍了,就给他报团去外地旅游。那十多年时光,是他今生最为幸福、最为轻松的一段岁月。家里生活的重担已经由我们去挑,腿脚轻快的他,可以到处去转。走州过县,四处观光,没人再嫌他误了农活,荒废了时间!儿女们这个让他去上海,那个让他去北京,他再也不用操心花销和费用;去看过苏杭的园林、北京的宫殿、桂林的山水后,他还有一个心愿,就是到山东的曲阜去拜拜孔庙。据说,距离那里不远的邹县,是我们族谱上可以追溯的源头。
去山东转一转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。几个孩子临近中考,几家人的心思就都放到了他们身上。那几年,父母亲是轻易不出门的。就是冬闲时邀请,他们也因为怕打扰孩子们的学习而一再拒绝。功成身退,这就是父母的品德!当我们不需要帮助时,父母亲是很难叫到城里来的。那时候,他们的借口很多:春天里放不下家里的花草,秋天里离不开地里的庄稼,即便是冬闲了,家里的狗和猫还没人照料。孩子上高中那几年,叫不来他们,我们一年也只回去两次,过年一次,放暑假一次,每一次来来去去,也都只是匆匆忙忙的一天时间。
孩子在合阳补习那一年,吃住在哥哥家里,需要他们每天给孩子做几顿饭。那一年,他们很干脆地到县城赔了孩子一年。我家孩子吃饭挑剔,一天几顿饭,父母都在尽心竭力地轮流去做。母亲变着花样做她拿手的家常饭,父亲每顿还少不了葱、姜、蒜齐备地动油锅炒菜。那一年,他们陪孩子度过了他人生中心情最灰暗的一段岁月。每天晚上,孩子要在学校里上晚自习,十点半下自习后,骑自行车十一点才能回到家。年冬天,一个冬天没有下雪,虽然不用担心路滑,但合阳的冬天依然很冷。每天晚上,孩子没回来,父母哥嫂一家人就一直不睡觉地看着电视、聊着闲话等着他回家。那一年,为了孩子,父母改掉了多年来早睡的习惯。
年,孩子高考一结束,父母立即打道回府,他们要赶紧回家去摘地里种的黄花菜,那可是他们那一年地里的主要收入。黄花菜很费事,一到花期,不论刮风下雨,每天都必须下地去摘。如果采摘不及时,花一旦开放,就吃不成了,就没人要了。为了雨天也能进地摘黄花菜,他们一人买了一双高腰的雨鞋。当遍地都是黄花菜后,深受其累的村人总结道:“要想死得快,就种黄花菜!”黄花菜从地里一摘回来就能换成现钱,但父母年龄大了,那种高强度的劳作早就不适合他们了。我家的黄花菜只种了两三年,就在大家的极力劝说下连根拔了。
孩子上大学后,丈夫把让父亲去旅游的几千块钱给了我,让我去找旅行社。他说,已经和父亲商量好了的,要以此报答父亲陪伴孩子那一年的辛劳。可母亲说:“千万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。他的记性、腿脚已大不如前。出了门跟不上人家,还让人担心!”“那你们俩一起去嘛!”“我不去,我晕车!一天到晚看电视,啥没见过嘛?!哪里还需要吃苦受累地跑出去去旅游?!”没人陪着出去,父亲出去旅游的承诺只好搁置。
随后,父亲又在城里给哥哥他们一家人做了几年饭。那是一段较为轻松悠闲的日子。看他爱吃羊肉泡,哥哥给他买了许多张羊肉泡的票,让他每天早上到街上去吃。中午,父亲会用心用意地做一顿家常饭,等着儿孙下班回家。晚饭,儿孙们大都有应酬,常常不回来吃饭。剩下父亲一个人,他随便吃点东西,就提上凳子,腿脚轻快地去公园里看自乐班演戏。那种神仙般舒心的日子,过了好几年。
几年后,父亲身体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。原本干净利落的父亲,渐渐地不爱洗衣服、也不怎么打扫房间了;接下来,他的耳朵出现了问题,有一段时间,跟他说话得大声喊叫、不断地重复;耳朵治好了,他的腿脚又明显地变慢。陪他上街,他东张西望看得很仔细,总是要让人不断地停下来等他。一条街走下来,很费时间。原本热衷于陪他上街的我,渐渐地有些心烦。老年人走路慢,可以理解。你停下来等他,他会走得更慢。两个人上街,他总是若即若离地保持着几步远的距离。让他一个人上街,他爱买东西却又不舍得花钱。陪他出去,我得领着他逛大商场、买上档次的衣物;他看上了什么东西,我得大包大揽地争着给他结账。有一次吃完饭从饭店出来,他又拖在我后边不远不近地跟着、东张西望地瞅着。我停下来生硬地问他:“你是走不快嘛?还是不想往快的走?”他黑着脸回答:“我不想走那么快!”
不久,进医院检查,父亲得了脑萎缩!啥?父亲问道。母亲说,也就是老年痴呆!一听这病的名字,父亲觉得有些伤脸面,他不让母亲随便对外人说。哥哥说,这病很难治愈,记忆力衰退、腿脚迟缓,许多症状只会越来越严重。我的心随之灰暗。
以后父亲不能单独出门了,再到外地旅游的计划彻底泡汤。一到节假日,大家都天南地北地出门去逛,我们只好开车带着他和母亲到周边的小景点去转一转。有一年国庆节,我们连哄带骗地把父母带到渭南周边的韩城、富平、蒲城转了几天,母亲虽然不太情愿,可父亲倒是兴致很高。
第二年“五一”,弟弟一家又带着父亲和他的岳父岳母去了山西。谁知一到王家大院,他岳母晕车晕得只想回家。那边的事还没处理完,到平遥古城后,刚吃完晚饭,一眨眼又把父亲给走丢了!一行人赶紧去找,找了半天没有找到,他们只好向街上的警察报案。警察说,得等24小时候后才能立案。大家心急火燎地找了半晚上,所幸的是,父亲最后被一个好心人开车送到了入驻的宾馆。有惊无险!大家长出了一口气。
谢过好心人之后,大家七嘴八舌地问父亲,怎么能一个人跑到城外那么远的地方去?父亲懵懵懂懂地回忆说,在饭店刚吃完饭,他一抬头,看见他孙子航航离开饭桌朝外边走,他赶紧起身紧紧追随。他喊了一声航航,也没听到回应。没顾上多想,他就一路快步紧跟着孩子朝前走。越朝前走人越少,还没想明白,前边的小伙子忽然不见了。那时候,再环顾左右,他早已出城了,城外的灯光也越来越少。他有些害怕,正在东张西望,前面不远处正好停着一辆白车。那辆白车的外观,跟弟弟的车很相似,他以为儿子在前边等着他,就急忙走过去。上前一看,结果不是自家人。看见他神色慌乱,开车的小伙子问他怎么啦?是不是迷路了?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小伙子忙安慰他说,老人家不要着急,你有家人的电话吗?可以打电话联系一下。父亲摸摸口袋说,手机没带,刚才放在饭店的房间里充电了。那你住在哪个宾馆?父亲搜遍全身找到了一张房卡。小伙子说,房卡上有宾馆的名字,只要知道你住在哪家宾馆里,我们开车把你送过去!就这样,父亲才又回到了亲人身边。
这件事,说出去有些丢人,父亲不让儿子孙子给我们说。大约半个月后,航航找我给他辅导作文,才说出了他们那一晚上让人心惊的奇遇。从山西旅游回来十几天了,关于这件事,父亲从没跟我们提起过只言片语。也许是怕我们担心,也或者嫌影响他的形象。谢天谢地!感谢那位好心的兄弟!感激之余,我在心中双手合十,默默地为老父亲祈祷!这也都是脑萎缩惹的祸!从此以后,父亲得寸步不离地有人跟着。
近几年,不常见他的人都说,一年一年他老得很快。脑萎缩捣乱之后,脑梗也来把他纠缠。几年间,变化最大的是他的腿脚。他不仅走得越来越慢,而且看起来头重脚轻的,很不稳当。尤其是上楼梯时,他已不会弯腰,他的身体总是在不由自主地往后倾倒。重心严重失衡,随时都有摔跤的危险。上楼梯危险,总会有人陪着。在门前的台阶上、在院子里的平地上走路,一不留神,腿一软,就摔了几次跤。每摔一次,身体就虚弱一点,行动就更不方便。
脑梗最害怕摔跤,我们给他买了一根拐杖。一开始,他嫌难看不愿意用。他说:“才刚上70岁的人,有多老嘛?就整天拄个拐杖!人还没老,都把人拄老啦!”可一旦出门走起路来,他的脚总像踩不实地一样,老往起翘。摔过几次后,他才在儿女们的一再劝说下,拿起了拐杖。
刚开始,拐杖在他手里显得很多余。一出门,他有些不会用拐杖。拐杖不是在身体的左右乱晃,就是像个没眼色的孩子一样,老是戳在他的前边,总在绊着他本来已不灵便的腿脚。看他这样,我觉得还不如我们扶着他走利索。那时候,他的拐杖经常靠在门后,备受冷落。
上台阶、上楼梯,无论大家咋样提醒,他的身子还是一直往后倒。为了他的安全,没啥大事,已经很少让他出门了。节假日全家人聚餐,需要上楼梯时,就得不停地给他教,要先把身体往前倾,然后再抬脚,等一只脚踩稳当了,再换另一只脚。这些教两三岁孩子的常识,要一遍一遍地说。就这样,他依然学得有些吃力。唉,老小老小的,人老了就又活回去了!人生是一个圆,老年之后,又回到了起点。在无奈地抱怨着他的时候,我忽然笑道,我怎么忘了,我学习走路的第一个老师,曾经就是他啊!不断重复的那些道理,他不是不知道,而是已经做不到了!
因为脑萎缩,他的记忆力也在迅速地衰退。一辈子对新东西接受比较快的他,慢慢地不会用手机了,即便是已经用了多年的非常简单的老年机。没意识到这一点之前,全家人都在私下里感叹,他怎么那么笨呢!那么简单的东西,为何怎么教都教不会呢?
父亲原来的手机坏了,弟弟给他买了个比原来更好的手机。我还提醒说要不要给他换个智能机?弟弟摇着头说,这个跟他原来那个手机的功能差不多,好学。可他就连这个都学不会,更不要说智能机了!
那款新换的老年机,儿子、孙子、孙女、女儿、女婿、未过门的孙媳妇,家里五六个人都曾不厌其烦地给他教过无数遍,就那么几个健,就只是接听手机、拨打电话这两种功能,说得大家口干舌燥,直到大家最后都泄了气,他还是没学会!回到老家,他又让左邻右舍的媳妇们教他,但最终,还是以失败告终。
每次他的手机一响,他就大呼小叫地喊着让母亲去接,或者把手机拿给她去听。正在忙活的母亲有时腾不出手,就让他去接,他拿着铃声不断的手机,手忙脚乱地不知所措。就这样,我们给母亲打电话,他有时还会因为没专门给他说话而埋怨生气。他给我告状说:“你妈自私得很,她只管她说哩,她就没想我也有话要说哩!”母亲说:“那你再打过去嘛!”父亲变脸了:“我如果会打过去,还用得着跟你说嘛?!”
前年冬天,把他和母亲接到渭南。母亲嫌麻烦我们不想来,一贯喜欢来渭南的父亲,第一次附和了母亲。那时候,除了脑萎缩、脑梗这两种病,前列腺疾病又来添乱。那种病,尿频尿急,一不小心就尿裤子,为此,他觉得不好意思见人。但见我们态度诚恳,他也就点头答应了。一坐在我家客厅的藤椅上,他就说:“我这次是来辞路的,以后可能再也来不了了!”这句话听得我们鼻子发酸,内心凄然。那个冬天,母亲整天给他洗裤子,他也觉得很没面子,尤其是在女婿面前。张锋知道后,说他见外,给他宽心。女婿对他的好,他心存感激。不久,他提出要去看张锋他爸。公公五年前也因脑梗早已半身不遂,行动不便。
对父亲的提议,我和母亲坚决反对。一个周末,张锋准备带父亲去他们家,我又站出来反对。他说,岳父已经向他提了五六次了,他不好意思再拒绝了。我转身对父亲说:“你们两亲家行动都不方便,都不能自理了,两个人到一起,他该照顾谁呀?”父亲说:“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,我是想去辞路的,以后可能就再没机会去了。”父亲这样一说,谁也不好再反驳了。张锋说:“没关系,咱自己开车跑一趟,也不是很麻烦的!”那一次去,他又受到了几家人的热情款待,吃了人家老弟兄俩两家的饭。回来后他满意地说,人家都很热情,饭菜也很丰盛。父亲一生为人热情、真诚,不管到那个亲朋好友家,都觉得人家对他不错。
最后这一次摔伤,也是为了顾及邻里关系才引发的麻烦。原先老巷里的东邻家添了个孙女,他们叫亲朋好友到镇上的饭店去吃席。爱热闹的父亲已经去不了,他硬要母亲去给人家道贺。母亲原本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,他说,就一顿饭的功夫,他不下床、不出门,在床上睡一觉你也就回来了。母亲推脱不掉,也就随其他人去了。
谁知,母亲走后,父亲竟然鬼使神差地下了床,出了门,坐在大门口和对门的本家侄子闲聊了几句。人家说完话回家去了,按说,咱也该回家去休息了。可是,不知道怎么回事,他居然一个人战战巍巍地下了门坡。走到巷道里干啥呀么?他想了一下,他也不知道。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的他,犹豫了一下,然后想转身回家。这一转身,已不再灵便的腿脚失去了平衡。腿一软,他摔倒在自己家的门坡坡底下。等再有人经过时,不知他已在地下躺了多久。几个过路的乡邻赶紧帮扶者将他抬回家,电话打过去,母亲赶紧跑回家。一看见躺在床上的他,才知道这次果真把麻烦惹下了。随即,住在县城的哥哥也被急招回家。那时候,父亲还不知道疼,众人也不知道他的伤势有多严重。几天后,叫医院拍了片子,哥哥这才用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mauritiustour.net/zyzljbsz/6539.html
- 没有推荐文章
- 没有热点文章